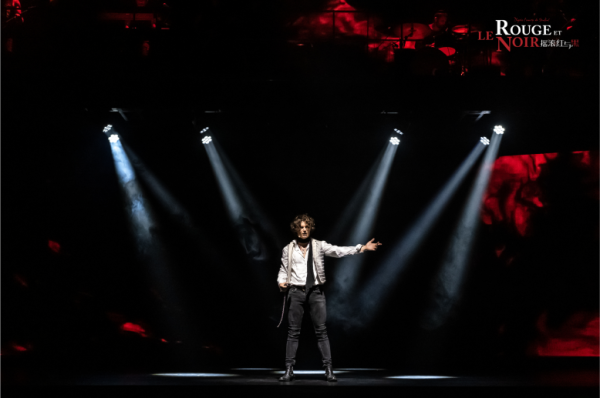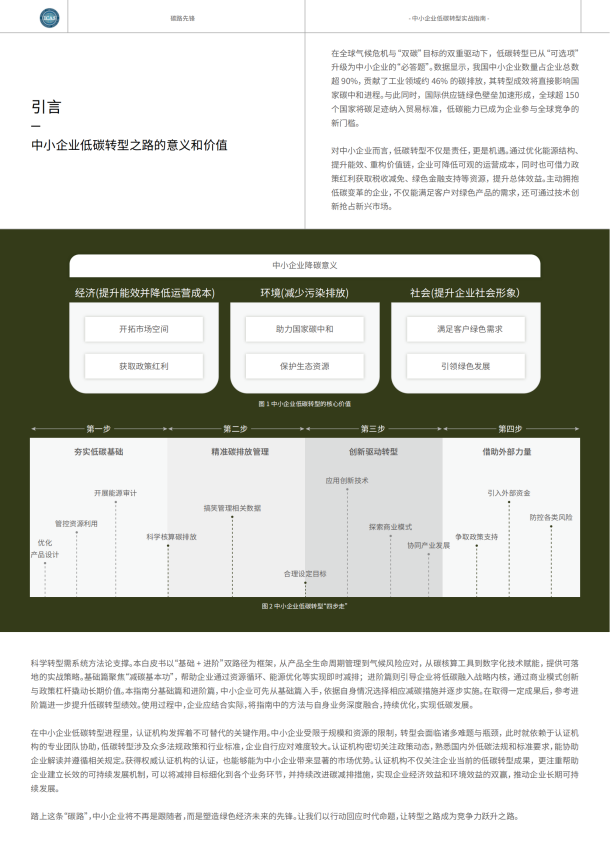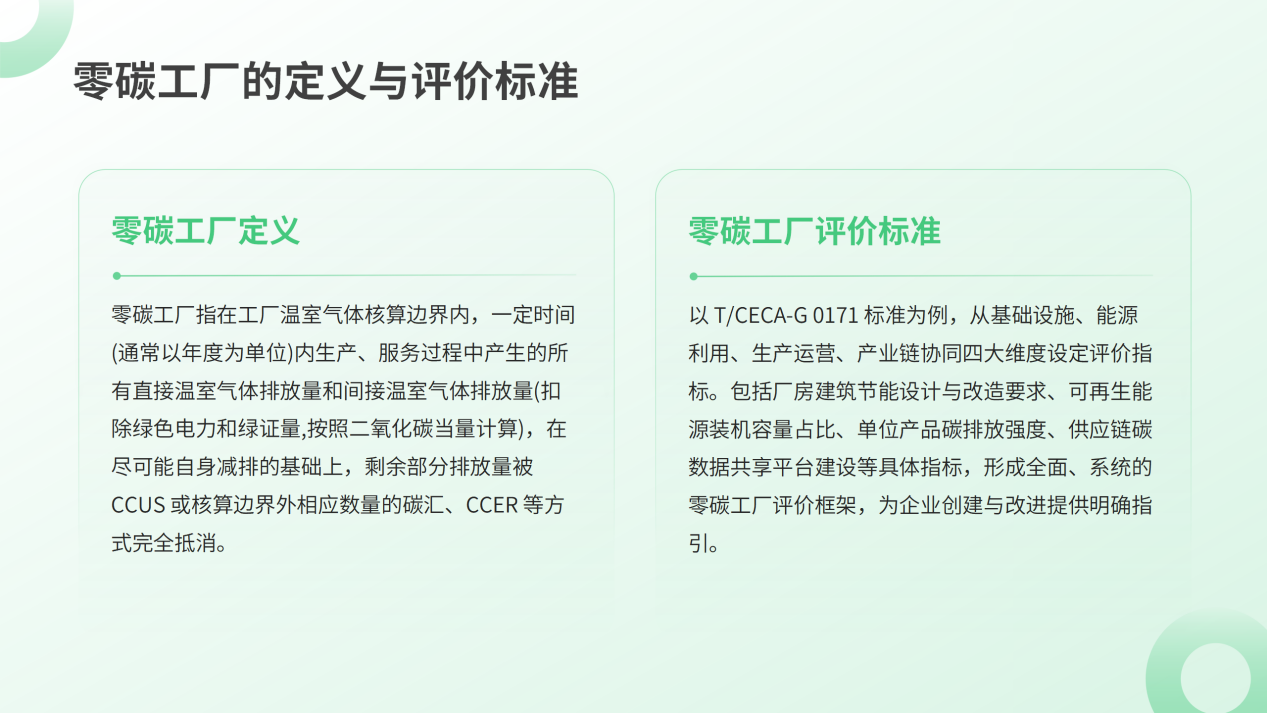有人类,就会有疾病,就会有医药。人类与疾病的抗争史,就是一部哲学史、文明史。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和文化,孕育了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卫生健康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中华儿女,我们有理由骄傲和自信,中医药是历经岁月沧桑、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文化瑰宝,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扮演着人类“守护神”的重要角色。
毛泽东曾说过,“中国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就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笔者很荣幸作为一名中医药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在几十年的从医生涯中,以医者仁心的态度、“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研发出全新的中医药成果,解除了许许多多人的病痛,为中医药行业规范化发展尽到一份绵薄之力。在未来,笔者愿与更多志同道合的中医药从业者一起努力,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做到“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在传承和创新两端齐发力,守护中医药文化这个瑰宝,更有力度地为健康中国助力,为全球卫生治理贡献“中国处方”。
半个世纪执着中医药
圣贤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确,每一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只要专注耕耘、持续拼搏,就一定可以开创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天地。
笔者出身于中医世家,自幼对中医药知识和文化兴趣浓厚。10年政治动荡时期,曾被安排到新华医院供应科劳动,此后又被安排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尽管日出日落劳作于红土地,却不忘学习中草药、傣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知识。后来,返城、上学、当教师,笔者在每一个阶段都留下了对中医药学的执着热爱。
不会,就勤学苦练;不懂,就钻研好问。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经过努力,终于自学考上大学,先后师承王锦云(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长、教授,肿瘤专家)、叶显纯(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上海十大名医、中医药理论家)、钟立贤(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药学系主任、药物学家),在肿瘤药学、药效学、药理、毒理及肿瘤临床医学和肿瘤防治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识。
弹指一挥间,笔者投身中医药研究和实践已有半个世纪。多年来,从事于中药的药学、药效学、药理学、毒理学、临床医学以及中医药防治肿瘤、白血病、艾滋病等方面的研究。
1986年起,出任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抗肿瘤新药研究课题的课题负责人;1992年,担任上海地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并先后受聘为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分会肿瘤防治研发基地负责人、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学术交流专家、美国国家教育医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讲座教授等职。
为规范中医药执业的标准化建设,笔者撰写并完成了《中医药诊断治疗肿瘤的标准及评价标准》,为指导我国中医药治疗肿瘤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操作准则。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元素,是可以与国语、国文、国粹、国宝相提并论的“国医”和“国药”。中国有文字可考的中医药学最早见于几千年前的先秦、汉魏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们经过探索、积累和总结,奠定了中医药的基础,进而造就了晋、唐时期的繁荣、丰富与提高。此后,经过两宋、金元时期的验证、整理和发展,特别是在医学理论体系方面的升华,又促进了明、清时期进一步的完善,形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医学”。
在历史上,中医药是中华民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重要力量。然而在近百年来,受西方殖民文化的入侵以及我国战乱连年、国贫民弱等方面的影响,中医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甚至一度处于被质疑、排挤、冷落、萎缩甚至不能正常发展进步的地步。这又进一步模糊了大众对中医药的认知,并加剧了中医药学术的混乱和纷争,使中医药鱼目混珠、真假难辨,最终导致了今天中医药和西医药相比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基于此,我国应该进一步重视教育国人客观、理性地认识国医、国药的内涵,加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令人振奋的是,中医药在应对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显示出独到的效果,被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不难想象,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需求的日益增长,中医药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承载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将发展成为朝阳工业。
守正创新 彰显自信
从事抗肿瘤研究几十年,笔者发现,在我国的医院里治疗肿瘤主要以西医为主,中医占比很低。往往是患者应用西医药治疗无望,才会以“试一试”的心态采取中医药治疗。而在中药中,只有一些扶正、调理和增效、减毒的辅助抗癌药,而没有可作为治疗性的具有抑制肿瘤功效的中成药,这不免有些缺憾。
在对癌症的治疗方面,很多西医治癌专家都认为或主张首选手术。笔者不反对必要的手术,因为手术对早期的治疗是有效的,但不是理想的方案,手术是创伤性的,对患者而言非常残酷。它只能割掉看得见的肿瘤,而割不掉看不见的肿瘤细胞,如果术后处理不当,复发和死亡的风险很大。
在对肿瘤类疾病进行了科学深入的分析研究后,笔者与团队展开了对抗肿瘤药材的筛选,按照国家制定的各种标准、规定,开展了对总课题所包含的30多个子课题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艰辛努力,特别在药学、药效学、毒理学、临床医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创新,达到了领先国际的技术水平。
肿瘤至今还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难重症,要发明一种有效的抗肿瘤药物必然是艰难的,仅以美国为例,其新药研究的成功率只有万分之一。因为药物要有效果,但有效却不能有毒性,即便药品是安全的,其质量控制是否能够得到保障?这又涉及药材品质、工艺处理等方面。
此外,在药物的临床试验中,笔者面临的一个关键难题是国内没有同类药品可做对照。此问题不解决意味着整个项目需要中止研究,前期投入的几千万元将一无所获。对此,国家有关药物审评部门提出要求用化学药物做对照,这种挑战极为苛刻严峻,因为不接受或者比不过就是失败。科学发现和发明的研究是探索性的,只有坚持才有可能成功。最终,笔者和团队击败了种种困难,获得了国家颁布的新药证书。此项成果被中国科学院查新、鉴定为国内首创、国际先进,还作为我国现代中医药新科技成果的代表参加了世博会的展示。
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巴厘·马歇尔教授(Barry Marshall)到中国访问时曾对笔者说:“我只不过发现了致胃部疾病的细菌,而你发明了治疗胃部疾病的药,中国的科学家真棒。”由于研究成果彰显东方医药魅力,凸显民族中医药精髓,笔者被美国的教育医学机构聘请为讲座教授,还受邀到印度、土耳其等国家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访问。
艾滋病是近20年来才被发现的一种病毒性传染病,虽然中医历代文献中尚无其名,但从其传播方式,流行情况、发病特点、临床表现等方面来看,与中医认为的瘟疫有相似之处,这种相关性为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治疗经验。就中医而论,笔者认为,艾滋病大致可分为4种癥型:气血双亏癥、气滞血瘀癥、瘀毒结滞癥和肺胃阴虚癥。当然,临床治疗应注重因人而异、辨证施治,这对治疗艾滋病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许多科学家认为治疗艾滋病的方法主要有3种:抗病毒药物治疗、免疫治疗和基因治疗,但至今效果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西药在耐药性及毒副作用方面存在不足,很多患者反而通过中医药的综合调理,在稳定和提高免疫力,改善症状,降低毒副作用,对各种并发症,如发热、乏力、咳嗽、腹泻、皮肤瘙痒、皮肤溃疡等有较明显的效果。这对提高生存质量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因人而异是中医学的精髓,是中医从宏观认识人体疾病和进行治疗干预的具体手段,它既是对疾病病情、病性、病势的基本反映,又是选方用药治疗的重要环节。很多医生从临床实际出发,应用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对艾滋病进行治疗诊治实践,取得了一定的临床疗效,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是针对艾滋病患者的症状而言的,在针对艾滋病病毒的研究方面并没有取得成功。
笔者在2006年就与广州中医药大学病毒实验室合作开展了针对艾滋病病毒的药物研究,并取得了基础性、决定性的成果。在对研发的3种抗艾滋病新药评价试验中,通过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初步鉴定了抗艾滋病中药的活性。在之后的重复性试验中,又肯定了抗艾滋病病毒的新药对抗原阳性细胞的功效,实现了抑制细胞病变,病毒产量显著下降的目的。目前,在前期基础上,笔者已经完成了总课题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产品有望在不久的将来上市,为解除艾滋病患者病痛作出贡献。
健康与医疗是最大的民生
“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笔者认为:“健康与医疗就是最大的民生。”中医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能得以繁衍,创造出如此辉煌灿烂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中医药文化濡养的结果。“与信人者,必先自信。”我们的文化自信,源于5000多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笔者坚信,我国以现代科技为引导的中药事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必将发展得越来越好。
科学是思想的产物,那么思维方式就是思想的基础。拿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进行比较会发现,中医药的思维方式是以哲学为基础的,是宏观的、辩证的、系统的、全面的,是以二元相对、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存在的。反观西医药是以解剖和实验科学为基础的,是微观的、单一的、具体的、局部的,是以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形成的。这就产生了起码两种不同的结果;中医要望、闻、问、切、听,要了解患者具体的病情和病症,首先要辨癥型,找出病因、病机,然后才是辨病,结合癥型和症状,确定治疗原则,有时还要考虑“急则治标”,再来考虑理、法、方、药,最后才能处方给药,产生疗效并恢复健康。这不是简单的安慰、安抚,或者治病救人的医德医术,而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运用结果。
西医药学的做法确实有比较科学之处,或者说比较快捷而简单,为了体现它的科学性,它必须只能依附于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现代科学技术,所以不管什么病先去做化验检查、影像学检查等,确定指标后再采取相应的治疗方式。
从前面所分析的内容可以看到,以生理机能结合病理机制为基础的东方医学和以形体实质的解剖为基础的西方医学,是相互独立的两种思想体系,进而产生的两种不同结果。
现在,可以明确这样的一种观点:“科学”也是相对的,昨天的科学可能是今天的科学,但也可能成为明天科学发展的障碍,所以,唯“过去式科学论”也是不科学的。
笔者及研究团队已研究明晰了肿瘤因虚、瘀、毒而发病的病机和病因,也针对性地研制了确实有效的治疗多种肿瘤的药物,既不增加患者的痛苦,也花不了多少钱,即便是晚期的患者也能做到有质量的延长,没有痛苦的离开。这是对人最大的尊重,也真正实践了人道主义精神。
很多年前,笔者就希望我国能进一步促进中西医二元化发展,让中医药真正在中国成为与西医药平起平坐的主流医学。同时,要认真地对中医药学在现代的发展状况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并按照中医药文化的发展规律加以继承和发展。今天,我们盼来了国家的声音:“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此外,我国制定出台的《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走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发展路子。挖掘民间方药,建设道地药材基地,强化质量监管。深化医保、价格、审批等改革,促进科技创新和开放交流。”这无疑又为中医药从业者点亮一盏“希望灯塔”。
笔者建议,为了有利于中医药事业创新,有必要从政策上、组织上、人事上、资源调配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创新。比如,强化管理审批部门的服务意识。从药品审批这个环节开始,要改变一流专家的科研成果(特指中药新药)由非一流专家评审的怪现象。因为医学和药物学是两个不同的科学门类,临床专家未必懂药,而药物学家必须懂这个病,才能发明相对应的药,所以,有“药物学家是临床专家的老师”的说法,但现实中相关职能部门对此理解还不够充分,这将是影响中药新药创新发展的一道坎。
对此,笔者建议国家进一步建立健全符合国情和中医药特点的有关药品的研发、审批、生产、质量、学术交流、临床应用、创新仿制、药品流通,以及药材种植、饮片加工等一系列规范化、标准化的管理性的政策与法规,达到有效管理、规范应用、正常发展。
笔者认为,要抓紧抓实药品的科学核价工作。纠正现实中存在的以次充好、药价虚高的混乱局面,经整顿以后,国家可以每年一次或几年一次地根据经济发展和药品价格浮动的指数发布调价幅度,把医药费用包括医疗费用纳入国家可掌控的范围,进而取消容易滋生腐败的药品招标,回归药品这个特殊商品的商品属性,改变国家财政上医保负担过重和不透明不可控的局面。
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除了继承、发展、提高、弘扬中医中药的科技含量外,还要加强“大国中医”的宣传教育,以古代医药学界先贤的名字命名,如设立国家级的“孙思邈医学奖”和“李时珍药学奖”等等,鼓励热爱和从事中医药的人士,为我国中医药发展而努力创新。
应该广开渠道培养、扶持、扶正中医药人才。为了适应未来医疗改革形势的需要,中医药的未来发展需要有一大批品学兼优、中医药功底扎实、医德高尚的年轻人、中年人,甚至有中医药专业基础、专科医术的老年人。中医教育必须符合中医药的规律,目前还有很多中医药院校的校长都是西医人士,要摒弃不中不西、不伦不类甚至全盘西化的所谓中医药知识的教育。同时,高度重视民间“郎中”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俗话说,“高手在民间”,“郎中”们“越老越吃香”,政府不仅要研究他们的药,还要研究他们的思想,激发他们为患者服务的积极性和专业性,通过开办短训班、成人班、传承班、函授班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掘、扶持、利用好这些民间郎中,创造好的环境和氛围,让更多的民间“郎中”能站到台前来,补足目前医药人才短缺的客观需要。
此外,建议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等主流媒体,加强宣传弘扬中医药文化,广泛开辟教育医学栏目,引导民众增强民族自信,振兴民族文化,提高自身的健康意识和知识,增强体质和生活质量,共同参与到“健康中国行动”行列。
一个健康的民族,是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长盛不衰。我们庆幸有中医药相伴相助“健康中国”,更寄愿中医药更好守护国人健康幸福,为推动中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写辉煌。(作者胡寅康系上海地康药物研究所所长)